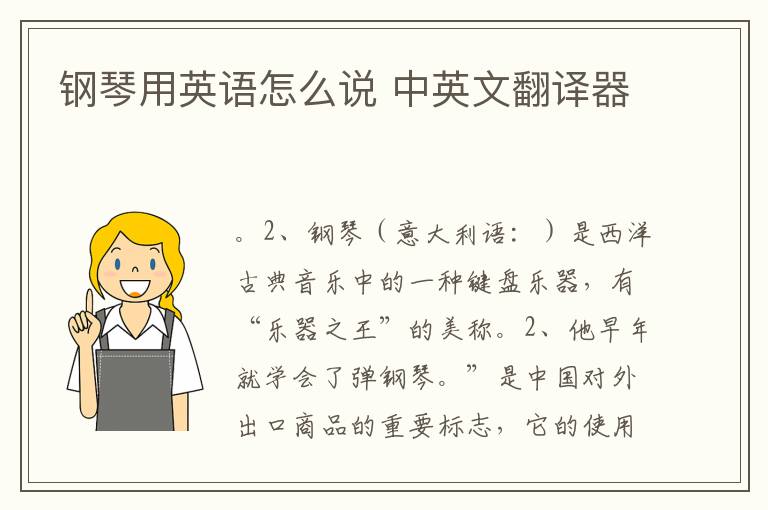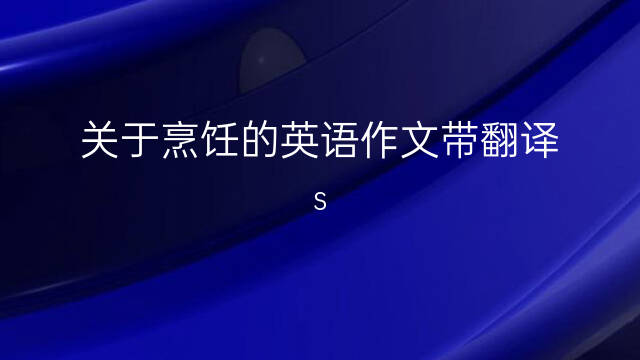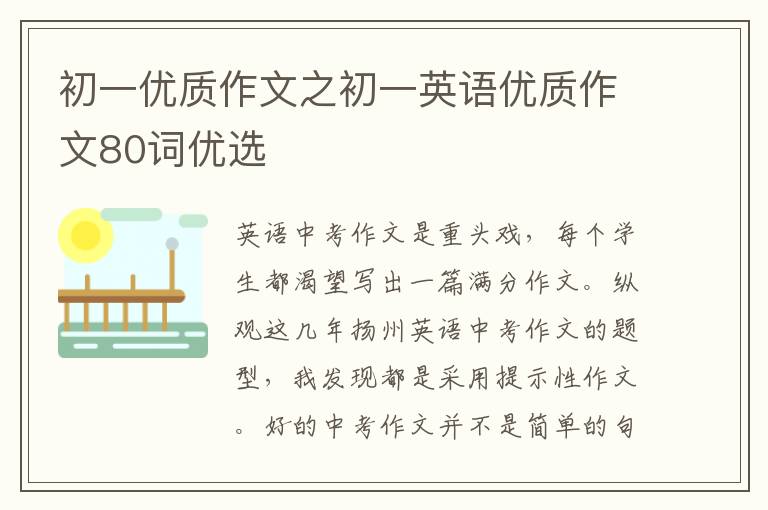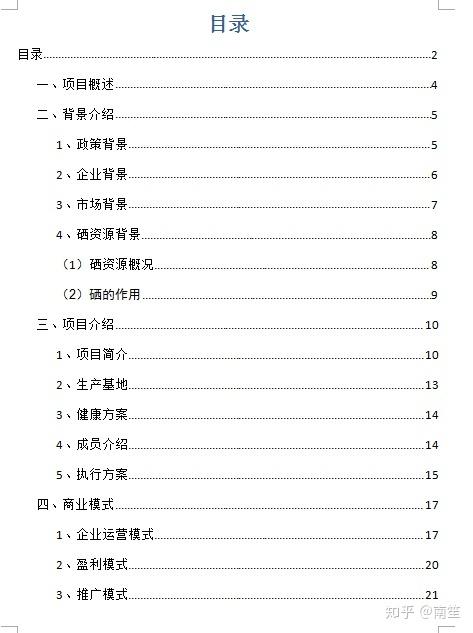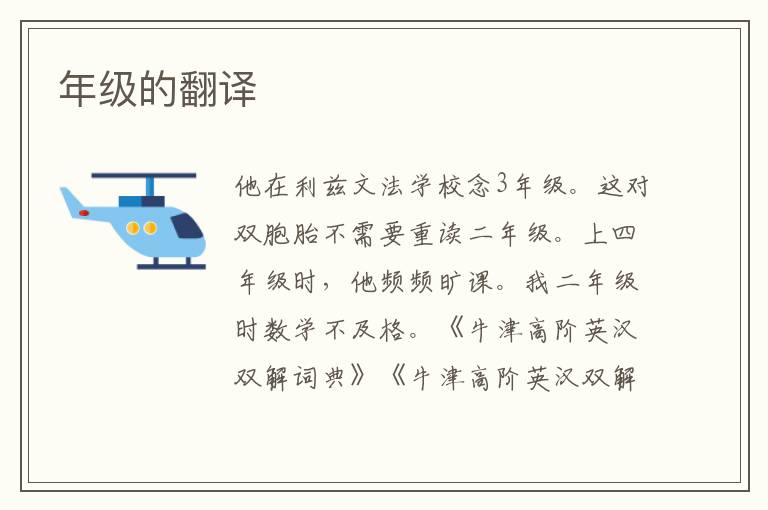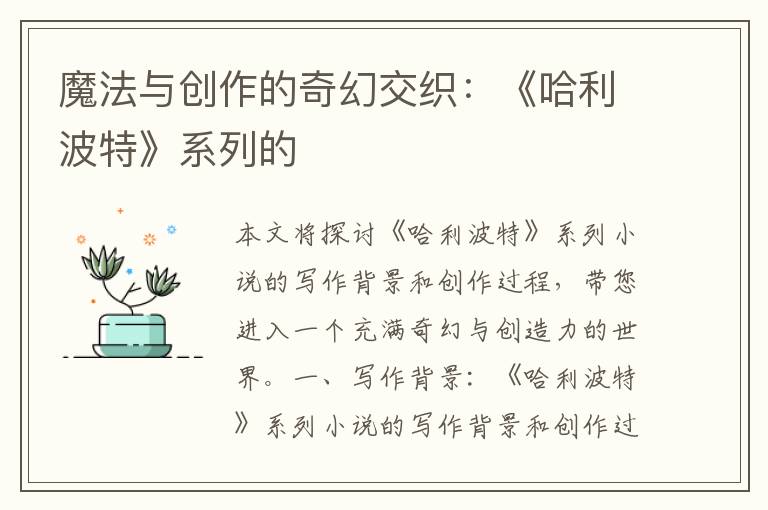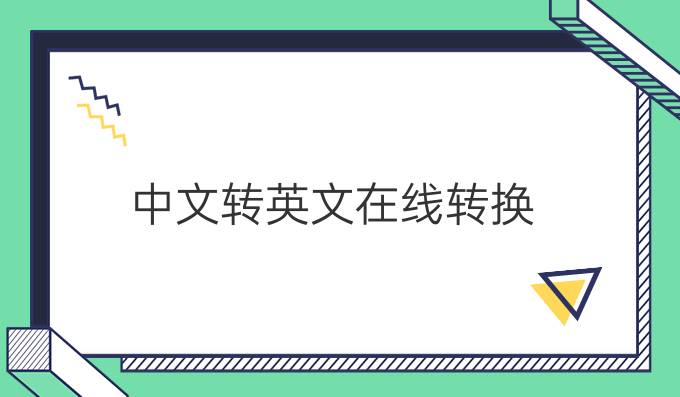我學了30年英語竟不如12歲的女兒

從美國回國前,我們全家到阿拉斯加自助旅游。那天,我們乘坐游輪出海看冰川,因風力太大,船顛簸得厲害,包括我太太和女兒在內的許多游客都暈船嘔吐,船長決定提前返航。上岸后,還沒完全緩過神來的女兒提醒我,剛才船上廣播說,游客可以到售票處去退錢。當時我只是隱約聽到廣播解釋縮短行程的原因并向游客致歉,并沒有注意到退錢一說。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我來到售票處,果然看到好多游客在排隊退款,我們一家子也退回了 100美元。
這是女兒英語比老爸強的一個實證。其實,在此之前她的英語表達已經明顯比我們家長強。我看她在家里給同學打電話,英語是脫口而出,連口音都和當?shù)氐暮⒆記]啥兩樣。哪像我這個學了將近30年英語的人,和老美交流起來還得邊想邊說,指手劃腳,盡管也能溝通,但總覺得不自如。
如果你說我英語很差,我是不服氣的。1983年高考,我的英語成績考了92分(滿分是100),是我所在那所縣城中學單科考分最高的。可我到了上海讀大學,見了老外連招呼都不敢打。1998年,報考副高職稱,按考綱復習了一遍,英語也考了90來分,可在采訪中總是避開老外,免得打完招呼后就沒話可說了。2002年,我首次隨團出訪美國,行前通過了全國出國培訓備選人員外語考試(BFT),但到了美國,連電視都看不太明白,和對方交流時更是覺得自己表達不到位。
像這種英語 高分低能的現(xiàn)象,我想絕對不是我個人獨有,可能是中國人學英語的通病。我記得,有一回我們在教會組織的免費英語口語班,美國志愿者讓大家做一個游戲――畫出你人生的成就圖,橫座標是時間,縱座標是成就感。在場的一位中國女博士畫的圖出人意料,因為她把目前在美國的點畫得最低,也就是人生的最低谷。我問她為什么,她說到了這里,人家說什么我聽不懂,我說的英語對方也不太明白,這對我的自信心打擊太大了。這位女博士通過了托福、GRE考試,掌握的英語詞匯量不少,看書沒有問題,但她說英語結結巴巴的,又帶有濃重的東北口音,可能加劇了她的自卑。
我女兒陳韻正從小學3年級開始學英語,可我?guī)Ю贤獾郊依飦硗妫思液退鼿ello,她卻躲到我背后,問她whats your name?,她也不回答。直到5年級上學期結束,她在國內學了兩年半的英語,盡管每次考試都是拿高分,但我沒見她在生活中用過一句英語。
11 歲那年,韻正隨我們到美國,插班到當?shù)匦W的5年級和美國孩子一起上課。每周5天,每天7個小時,在學校這么一個純英語的環(huán)境里,她不得不去聽,不得不去說,不得不去看,不得不去用英語做作業(yè)。有一次,我到學校接她,看到她和同學們邊跳繩邊唱著兒歌,特別好聽。我想,在玩中說,在玩中唱,恐怕是學英語的最好方式了。大約3個月后,我發(fā)現(xiàn)她在和美國人交往時已經能說一些英語了,盡管帶有老家的口音,但表達起來比我自然。
半年后,韻正迷上了英語小說,她自己有公共圖書館的借書卡,就自己上網去查找、預約,把某作家寫的小學生的故事,能借到的都一一借回來,總共看了不下50 本。大量的閱讀,對她英語表達能力的提高大有幫助。一年后,我發(fā)現(xiàn)她似乎更喜歡用英語來思維,包括寫日記也改用英語了。回國前的最后一次家長會上,我私下問老師,韻正的英語綜合水平和美國同齡孩子比,怎么樣?老師告訴我,大概低一個年級。
在美國一年半時間,女兒的英語接近當?shù)睾⒆拥哪刚Z水平,更是大大超過了我。我想,這不僅與她年紀小容易學語言有關,更重要是我們兩代人學外語的方法迥然不同。
我小時候學英語是把它當做一門學問來學的――記單詞,背語法規(guī)則,考試時又把它當做像數(shù)學一樣來推理――什么填空題,改錯題,判斷題,把語法的規(guī)律掌握后,運用數(shù)學的邏輯推理就能搞定。即便是聽力,只要掌握了題型,靠猜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考過舊托福的人都知道,Pizza總是難吃,Pie總是好吃,男生愛吹牛,愛Show off,愛喝酒,愛Party,不愛上課,愛找女生借筆記,反正就是不干好事;而女同學則個個都是完美主義者的化身。熟捻考經人往往能考出高分,但到了美國難免會碰到像上述女博士那樣的煩惱。
再來看看我女兒韻正在美國學習英語的過程:先是大量地聽,然后慢慢開口學著說,接著是自己找書看,并學著寫日記。這種學習外語的方式和咱們學母語的過程完全一樣,它是符合語言規(guī)律的,所以才是行之有效的。
韻正回國后,校長特準她可以在英語課上看課外書。她就利用英語課的時間,把原先在美國用中文寫的30多篇文章,逐一翻譯成英語。每個周末,我?guī)竭@里的一個美國朋友家,和他們的孩子一起玩,并請美國朋友幫她修改作文。現(xiàn)在韻正已經在《雙語周刊》、《英語沙龍》等報刊開設了個人專欄,她渴望不久能出版一本屬于自己的中英文雙語書。
我女兒有幸走出了學英語的誤區(qū)。但是,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把英語當學問來研究的習慣依舊未改。這不僅貽害了我們60后,而且還在繼續(xù)危害下一代。我看到,90后的中國孩子們學的還是啞巴英語,還在重蹈覆轍。因為我們的教育工作者把學生首先定位為英語學習者,而不是英語使用者。這種本末倒置,必然導致英語教育的失敗,只能培養(yǎng)出一批像我這樣高分低能的標本。
從美國回國前,我們全家到阿拉斯加自助旅游。那天,我們乘坐游輪出海看冰川,因風力太大,船顛簸得厲害,包括我太太和女兒在內的許多游客都暈船嘔吐,船長決定提前返航。上岸后,還沒完全緩過神來的女兒提醒我,剛才船上廣播說,游客可以到售票處去退錢。當時我只是隱約聽到廣播解釋縮短行程的原因并向游客致歉,并沒有注意到退錢一說。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我來到售票處,果然看到好多游客在排隊退款,我們一家子也退回了 100美元。
這是女兒英語比老爸強的一個實證。其實,在此之前她的英語表達已經明顯比我們家長強。我看她在家里給同學打電話,英語是脫口而出,連口音都和當?shù)氐暮⒆記]啥兩樣。哪像我這個學了將近30年英語的人,和老美交流起來還得邊想邊說,指手劃腳,盡管也能溝通,但總覺得不自如。
如果你說我英語很差,我是不服氣的。1983年高考,我的英語成績考了92分(滿分是100),是我所在那所縣城中學單科考分最高的。可我到了上海讀大學,見了老外連招呼都不敢打。1998年,報考副高職稱,按考綱復習了一遍,英語也考了90來分,可在采訪中總是避開老外,免得打完招呼后就沒話可說了。2002年,我首次隨團出訪美國,行前通過了全國出國培訓備選人員外語考試(BFT),但到了美國,連電視都看不太明白,和對方交流時更是覺得自己表達不到位。
像這種英語 高分低能的現(xiàn)象,我想絕對不是我個人獨有,可能是中國人學英語的通病。我記得,有一回我們在教會組織的免費英語口語班,美國志愿者讓大家做一個游戲――畫出你人生的成就圖,橫座標是時間,縱座標是成就感。在場的一位中國女博士畫的圖出人意料,因為她把目前在美國的點畫得最低,也就是人生的最低谷。我問她為什么,她說到了這里,人家說什么我聽不懂,我說的英語對方也不太明白,這對我的自信心打擊太大了。這位女博士通過了托福、GRE考試,掌握的英語詞匯量不少,看書沒有問題,但她說英語結結巴巴的,又帶有濃重的東北口音,可能加劇了她的自卑。
我女兒陳韻正從小學3年級開始學英語,可我?guī)Ю贤獾郊依飦硗妫思液退鼿ello,她卻躲到我背后,問她whats your name?,她也不回答。直到5年級上學期結束,她在國內學了兩年半的英語,盡管每次考試都是拿高分,但我沒見她在生活中用過一句英語。
11 歲那年,韻正隨我們到美國,插班到當?shù)匦W的5年級和美國孩子一起上課。每周5天,每天7個小時,在學校這么一個純英語的環(huán)境里,她不得不去聽,不得不去說,不得不去看,不得不去用英語做作業(yè)。有一次,我到學校接她,看到她和同學們邊跳繩邊唱著兒歌,特別好聽。我想,在玩中說,在玩中唱,恐怕是學英語的最好方式了。大約3個月后,我發(fā)現(xiàn)她在和美國人交往時已經能說一些英語了,盡管帶有老家的口音,但表達起來比我自然。
半年后,韻正迷上了英語小說,她自己有公共圖書館的借書卡,就自己上網去查找、預約,把某作家寫的小學生的故事,能借到的都一一借回來,總共看了不下50 本。大量的閱讀,對她英語表達能力的提高大有幫助。一年后,我發(fā)現(xiàn)她似乎更喜歡用英語來思維,包括寫日記也改用英語了。回國前的最后一次家長會上,我私下問老師,韻正的英語綜合水平和美國同齡孩子比,怎么樣?老師告訴我,大概低一個年級。
在美國一年半時間,女兒的英語接近當?shù)睾⒆拥哪刚Z水平,更是大大超過了我。我想,這不僅與她年紀小容易學語言有關,更重要是我們兩代人學外語的方法迥然不同。
我小時候學英語是把它當做一門學問來學的――記單詞,背語法規(guī)則,考試時又把它當做像數(shù)學一樣來推理――什么填空題,改錯題,判斷題,把語法的規(guī)律掌握后,運用數(shù)學的邏輯推理就能搞定。即便是聽力,只要掌握了題型,靠猜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考過舊托福的人都知道,Pizza總是難吃,Pie總是好吃,男生愛吹牛,愛Show off,愛喝酒,愛Party,不愛上課,愛找女生借筆記,反正就是不干好事;而女同學則個個都是完美主義者的化身。熟捻考經人往往能考出高分,但到了美國難免會碰到像上述女博士那樣的煩惱。
再來看看我女兒韻正在美國學習英語的過程:先是大量地聽,然后慢慢開口學著說,接著是自己找書看,并學著寫日記。這種學習外語的方式和咱們學母語的過程完全一樣,它是符合語言規(guī)律的,所以才是行之有效的。
韻正回國后,校長特準她可以在英語課上看課外書。她就利用英語課的時間,把原先在美國用中文寫的30多篇文章,逐一翻譯成英語。每個周末,我?guī)竭@里的一個美國朋友家,和他們的孩子一起玩,并請美國朋友幫她修改作文。現(xiàn)在韻正已經在《雙語周刊》、《英語沙龍》等報刊開設了個人專欄,她渴望不久能出版一本屬于自己的中英文雙語書。
我女兒有幸走出了學英語的誤區(qū)。但是,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把英語當學問來研究的習慣依舊未改。這不僅貽害了我們60后,而且還在繼續(xù)危害下一代。我看到,90后的中國孩子們學的還是啞巴英語,還在重蹈覆轍。因為我們的教育工作者把學生首先定位為英語學習者,而不是英語使用者。這種本末倒置,必然導致英語教育的失敗,只能培養(yǎng)出一批像我這樣高分低能的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