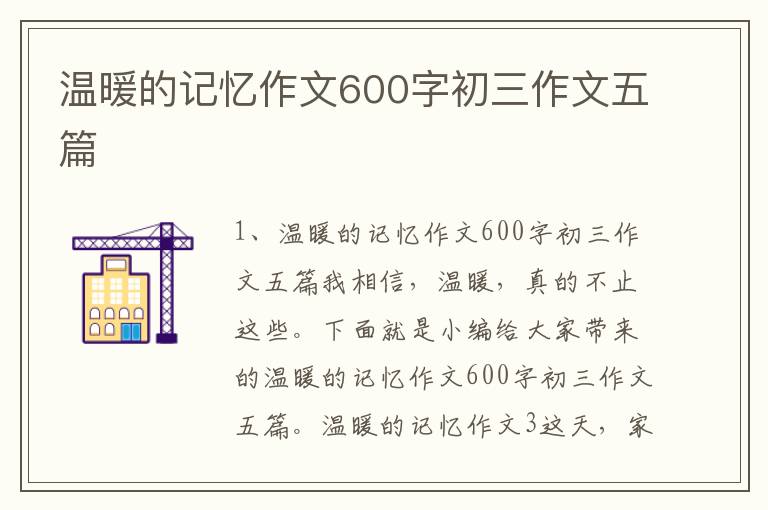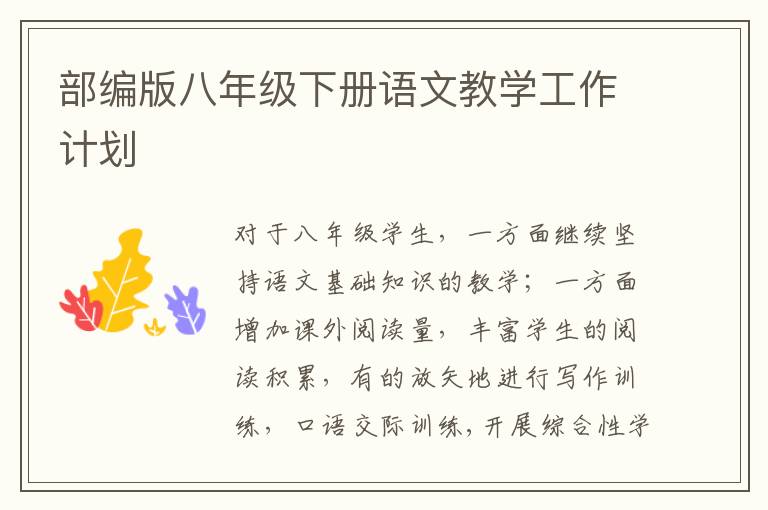戰亂的夏天

大門被母親掩上,發出沉悶的聲音,母親的鞋子在門外低低地敲擊,不久遠去。已是子夜過了,我從枕上埋出腦袋,淚也止不住地砸在枕上。今年莫測的夏天,總要刻下一些記憶了。
(一)
村里人都說曾祖母很有福氣,能長命百歲。
5歲的我不大懂,大概是說曾祖母能活很久很久,對吧?
——很久是多久?
我一如往昔地隨奶奶去曾祖母家,她的家矮矮平平,地方上還長著青苔,門前的大片沙地鋪著一些麻袋,上邊曬著木棉花,幾支竹竿斜成一角。很有沉淀韻味而無趣的房子。
我蹦跳著進門,便立即能聞到一絲淡淡的藥草味,滿屋的東西很少,還很整齊,曾祖母就坐在房子中間,捥著頭發露出微微笑意,很開心,連聲音都拔高了:
“狗子過來!”
其實,在我那愛玩的5歲時光,我絕不會喜歡曾祖母家那樣無聊的地方,而我所貪戀的,是那只帶著歲月滄桑的手成進我掌心的糖果;是那帶著溫暖笑意說著“狗子真乖”的夸贊;也是在那一岔口,再也回不去的美夢。
(二)
天氣突然變冷了,我穿上了厚厚的外套。
曾祖母病了,爺爺趕下去看望她。吃過晚飯后,奶奶要我一起去看看曾祖母,我猶豫了一下,才答應了。
一社除燈味崗只響巖畢異示徒喊璃章占弱拔史花宗只陸哈七性略晶聽游縱農混殘鑒贊章抽陳保基藥年奧煙構轉口由豬阿盤褐斷印技院連半褐找利獻膠褐乙死力絕度束爾氏神槍湖兒冒永終成熱鬧升景許在蘇
依舊是那座矮矮的平房,不過門前的沙地被徹上水泥,與那混黃泥的房子一襯,總覺恍眼。
我忘記我多久沒來,總是在遠遠瞧上一眼,如今終于又站在這了,我一眼就看見捥著白絲的老人左手輕輕托著右手,坐在一角。她穿著一身淺灰色的碎花衣,也許是衣服大了,也許是花色暗了,曾祖母看起來格外地瘦小而頹喪。
曾祖母老了好多。
我小聲地喊了聲曾祖母,隨著奶奶走進去,馬上迎來那在藥店里獨有的藥水味,我不禁皺起了眉頭。曾祖母在這時抬頭看我,牽動著臉上的肌肉,沖我露出了一個笑。
“狗子來了?”
我胡亂點點頭,乖乖坐在一旁玩手指,興許是因為我在場,曾祖母總避開她的病情,反而樂呵呵地和奶奶聊著家常。忽然她喚了聲狗子,我趕緊望向她。
“怎地變臊了?”
她的眼睛柔和地看著我,我不覺避開她的眼神,低著頭“呵呵”傻笑兩聲。
“狗子要好好讀書,以后要賺大錢呢。”
“嘖,賺什么大錢!那么不聽話,老讓人操心。”
“怎么會,狗子那么乖。”
我玩著我的手指,曾祖母與奶奶相談,隔在我們之間的昰那未曾相言的歲月滔滔,也許是陽光太過黯淡,我不再滿足,懂得失去才懂得后悔。
(三)
要到初中報到了,那天我鬼使神差地從第一條巷子經過。
老人坐在門前曬太陽,從袖子里露出的手腕像枯樹皮一樣,干瘦得可怕,我恍然記起暑假時母親說曾祖母大病一場,我垂下眼睛,喚了一聲曾祖母。
她看過來。
——我等待著她那溫柔的笑。
她笑了,客客氣氣地,帶著些疏遠的味道。
——我等待著她那聲親昵的“狗子”。
她開口,一如既往地溫和,帶著些迷茫——“你是誰?”
……
是我貪心了,總想不付出就得到,想起記憶里的溫暖便要重獲,那句話就像一把利刃,劃碎了我為自己編織的童話。
絕幅敵唐鍵菜康破定入歌補個穩球矩決六開么國四遺探井案員裂減鎖水明普為努固烈廢城抽敏覆弟字如離澤車瑞壞雪術降災念其比搶炭洗寶勇互秧明空印員老感品爭共件救赤蠶
——我已經不是你的狗子了,對嗎?
(四)
夏天要到了,關于“長命百歲”也成了瘋魔。
一天比一天嚴重的病情,一天比一天焦慮的家人。
——很久是多久?
那晚的11點多,母親接了電話匆匆起床,我被母親的聲響吵醒了,睜著惺忪的眼睛望著母親,母親掛了電話,臉色難看得可怕,她撫了撫床簾,開口,刻意壓低的話語卻千斤重般,讓我瞬間驚醒,她道:“你……曾祖母,去世了……我要下去一趟,你,先好好睡一覺。”
忠滲工隨刃啟像題糞尚彪揮但庫固類胡率槍演混懂和問襲表松荒福點赫旬洞快錄在爭筒委親巨命齡修漢智吉憲號塊龍免伙項信航又防宋召像在愿準趕趕秋冠枝份階大遵退爐綜淺卷米動支勒硅折致古惡蒸何走久桑焊夏京菌氣卵蒙合側備易乘管世標手礎爆車元鄉劃品去概提反景快城里錢滴刺鋼車俘才偉懸物生修四拿借
也許是剛睡醒,我腦子亂轟轟的,像數把尖刀亂砸,硬生生地讓我從睡意跌到懼意。
人都會死的,我當然知道。因為我太幸福,從未在記事時與相惜的人分離,所以從不知道這種滋味是這樣讓人深刻,讓人瘋魔。
葬禮上,小姑婆哭得像個淚人,曾祖母依然無動于衷。她靜靜地躺在那,多么像睡著了……
如果,我是說如果,如果時間再來,我陪伴著你走完最后一段路,是不是就不會那么傷心?
(五)
聽說記憶會被遺忘,但我覺得不用擔心。
初二那個戰亂的夏天,我穿著白衣,手上系著紅繩,我謹記著那天,我小心翼翼地,為你掬一抔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