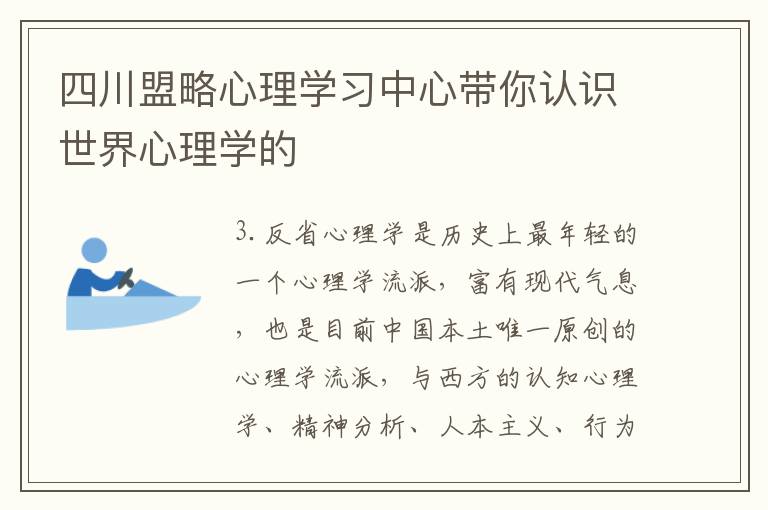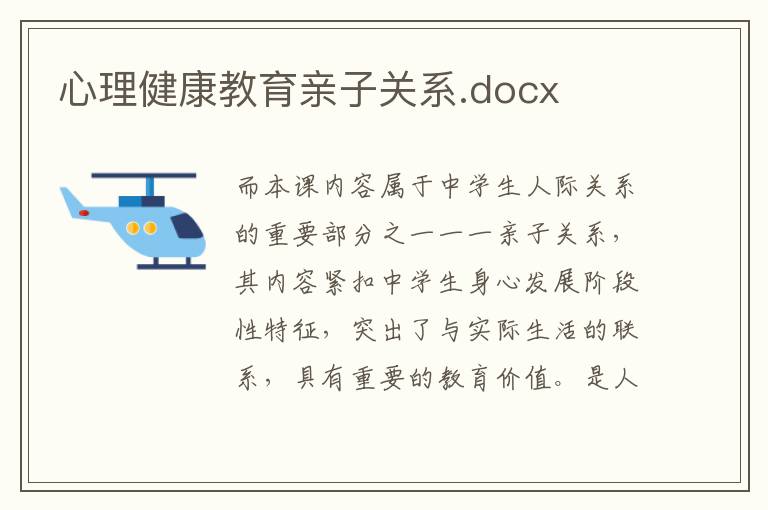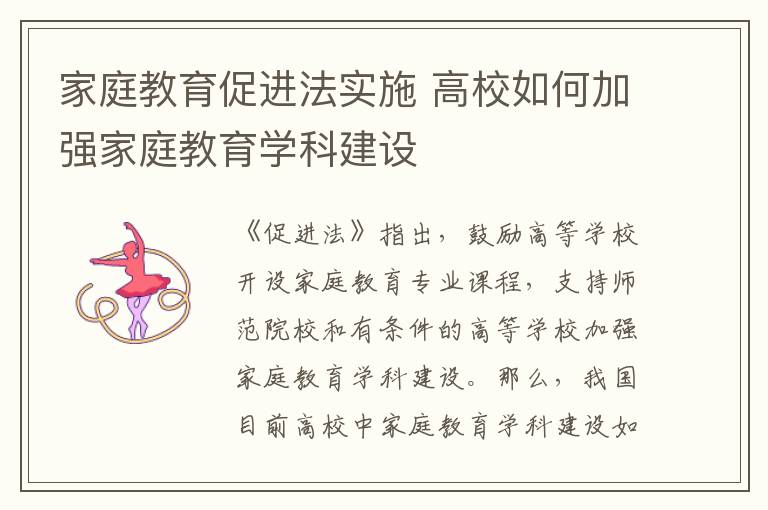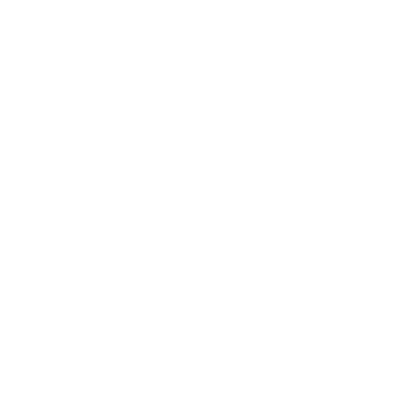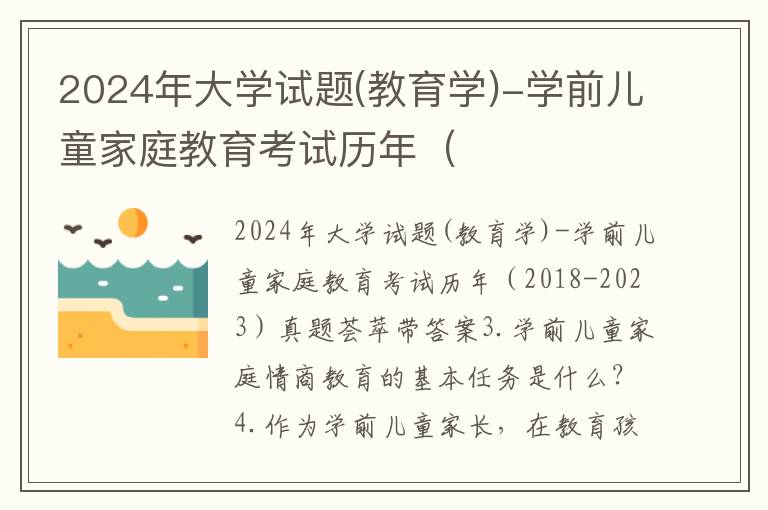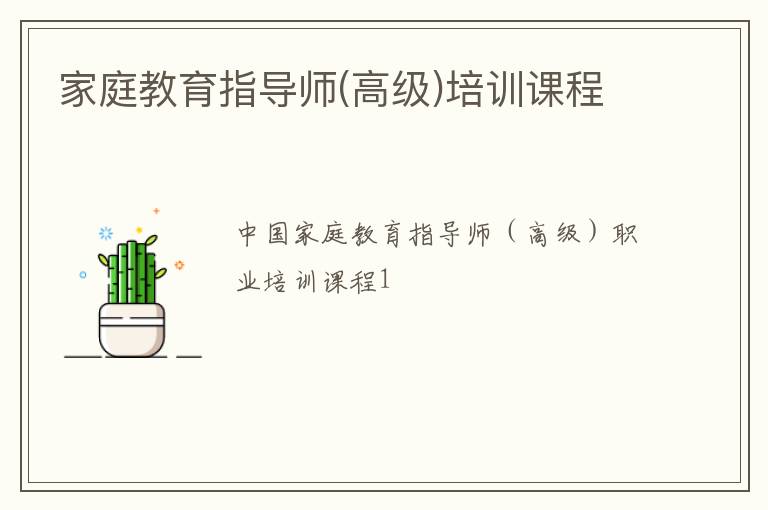家庭教育劇:屢上熱搜之余更需有冷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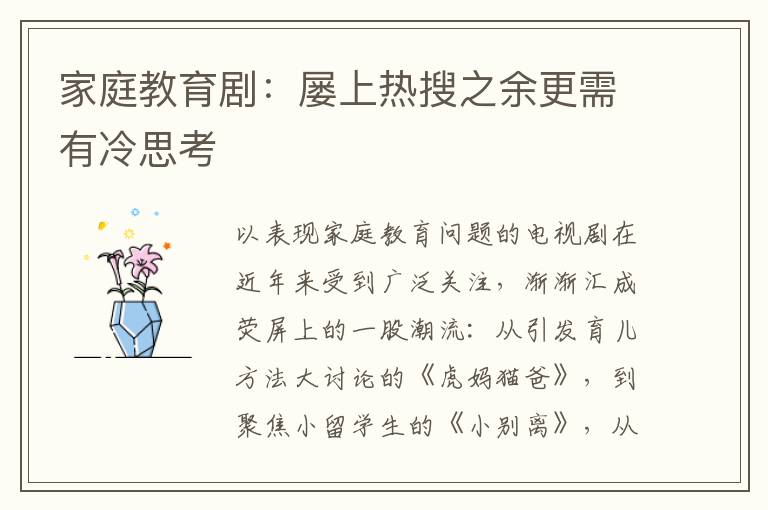
以表現家庭教育問題的電視劇在近年來受到廣泛關注,漸漸匯成熒屏上的一股潮流:從引發育兒方法大討論的《虎媽貓爸》,到聚焦小留學生的《小別離》,從關注高考問題的《小歡喜》,到展現青春成長的《以家人之名》,也包括正在播出的《陪你一起長大》《小舍得》以及待播劇《學區房》等。它們以展現家庭關系折射當今與教育相關的社會生活,切中夫妻關系、親子關系,育兒問題、家庭教育問題、學校教育問題等等諸多“痛點”,輕而易舉就能引發廣泛關注,相關話題總能從劇中的人物情節延伸到劇外的現實生活。
隨著家庭教育越來越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此類家庭教育題材電視劇的出現,正是創作者有意識對這一社會現象做出的敏銳反應。但需要關注的是,在頻頻因精準抓取的社會熱點話題登上熱搜之余,劇作本身不能陷入一種“典型化+輕喜劇”的套路,否則予人的驚喜、回味與思考會越來越少。如何沖破這種套路,或者開掘這一“組合拳”的新活力,值得創作者進一步探索。
以教育問題作為引線、“媽圈”作為聚焦視點,找到當下社會生活“最大公約數”
“孩子可以輸在起跑線上嗎”“平衡家庭和事業有多么難?”“媽圈凡爾賽”“爸爸帶娃災難現場”……《陪你一起長大》自播出以來,持續貢獻熱搜話題。該劇以帶有溫情甜味的“輕喜劇”方式,講述同一個學區四個不同家庭面對“幼升小”的教育故事。這四個家庭頗具典型性,幾乎涵蓋中國家庭的大部分面向,讓每一個家有學齡兒童的觀眾似乎都能從中窺見熟悉的影子:蘇醒和奚彬組成“學霸”家庭,兒子卻是“學渣”;林蕓蕓和顧家偉的家庭充斥著中產階層的精英氣息,也導致他們對女兒的高標準、嚴要求;何景華和蔣博是男弱女強的重組家庭,姥姥和姥爺的隔代教養讓他們的孩子成為了“小破壞王”;沈曉燕和李翔的離異家庭同樣切中當前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而他們的孩子是不折不扣的“牛娃”。如此,該劇以群像的方式展現家家都有的“難念的經”,交織出一幅頗具戲劇張力的育兒百像圖。
與此同時,《陪你一起長大》并沒有單純聚焦家庭教育問題,而是將教育問題作為重要引線,以“媽圈”作為聚焦視點,以“一鍋燉”的方式完成對諸多典型社會話題的雜糅,從“雞娃”“媽圈”到學區統籌,從面臨家庭與事業平衡的媽媽到“消失”的爸爸,這也是其引起大眾共鳴的重要原因。例如,掌握家庭內絕對話語權的顧家偉,在與金牌設計師蘇醒初次見面的一場對手戲,就捕捉到當下許多女性的現實處境。當顧家偉質疑身為媽媽的蘇醒不可能對工作全力以赴時,被反問自己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他回答“我負責賺錢養家,我太太負責貌美如花”,蘇醒則以“所以說顧先生的成功,是以犧牲太太的事業而成就的”予以回擊。一方面,社會默許了女性負責家庭和育兒的“潛規則”,也導致已婚職場女性給人留下生產力低下的刻板印象——劇中蘇醒與顧家偉的這場爭鋒正是女性主體對這樣一種不平等社會現狀的有力揭示;另一方面,以林蕓蕓為代表的全職媽媽面臨著與男性家庭地位不對等的境況——在外,她是“媽圈”中的“頂流”,是受人尊敬的“顧太太”;在內,她面對丈夫只能唯唯諾諾,低聲下氣,也直接導致她在家庭中的“失聲”狀態。
對典型人物、家庭的刻畫,是《陪你一起長大》觸發觀眾共鳴的基本前提,借由人物身份、家庭境遇的相似性,觀眾很容易將自身映射至某一形象中去,實現與影像的“縫合”。對典型社會話題的敏銳洞察與真實再現,則讓該劇引發觀眾心理共鳴,劇中借由教育問題引發的對家庭、婚姻、夫妻、職場、男女地位等多種社會問題的展示,可謂當下社會生活的“最大公約數”,進而掀起大眾討論的熱潮。
“典型化+輕喜劇”漸成家庭教育劇“套路”,如何往前再邁一步值得思考
選取幾個典型的家庭,配以輕快的敘事——近些年家庭教育題材的電視劇漸漸形成一種“典型化+輕喜劇”的模式,《小別離》《小歡喜》《少年派》《以家人之名》以及《陪你一起長大》莫不如此。
在這種“典型”的塑造之下,不難總結出一套人物設置的框架:往往有一個家庭是富有的,一個是小康的,還有一個是較為困難的;往往有一個家庭父母相處和諧,一個雙親離異,還有一個家庭重組等等。這種設定帶來不同的演繹視角,確實容易盡可能網羅現實,切中大多數觀眾的處境,讓人在劇中找到認同感。但當一味“抓典型”成為“套路”,局限性也愈發凸顯,不僅漸漸讓觀眾對這樣的典型組合喪失興趣,更無法呈現真實社會的多元化與多樣性。
而“輕喜劇”的敘事方式則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以喜劇化“糖衣”打磨了一些社會問題的尖銳棱角,使觀眾更加樂于接受,另一方面又容易將這些問題簡單化,削減此類劇作對思考家庭教育與剖析社會問題的精度與力度,使社會現實淪為影視中一道“漂浮的景觀”。
家庭教育劇尋求突破,或許可以從這樣幾方面著力:
首先,多個家庭的多個故事不妨在敘事的深度與寬度上齊頭并進。《陪你一起長大》講述的四個家庭的故事,可謂面面俱到,觀眾卻容易在四個故事之間“應接不暇”,來不及展開更多思考。倒是《小舍得》做出了一些新的嘗試,一改這個系列前兩部《小別離》《小歡喜》以各個層面三個家庭為樣本的模式,通過大家庭內部三代人的糾葛來展現教育問題。作品將親子關系、夫妻關系、代際關系雜糅在一個共同的大環境之下,將多個家庭的“寬度”和家族內部的“深度”進行了一種融合。
更重要的是,“典型”應該具有典型性。這不僅僅包括典型的人物外在形象、性格特征這些浮于表面的東西,更重要的是人設內核的立得住。例如《都挺好》雖不是家庭教育劇,但劇中“巨嬰”蘇大強的人設或許值得借鑒。看上去,蘇大強是一個不講道理、胡攪蠻纏,專給兒女拖后腿的老頭,而他的內里其實是一個壓抑、懦弱的老人。這樣的人物之所以顯得豐滿,不僅因為他有著獨特的外在形象,更因為劇作對其內在精神肌理的細膩刻畫。而在《陪你一起長大》中,胡可飾演的何景華則似乎成了一個有些“崩”的媽媽形象,這來自她身份上的矛盾。在外她是游刃有余混跡媽媽圈的“人精”,但回到家,她對自己孩子的事并不上心,總依靠他人來解決相關問題——一個看上去情商智商“雙在線”的人物,時常做出不符合其設定的怪異舉動,帶來許多割裂感。
除此之外,若以輕喜劇來講述社會問題,如何講得不膚淺、不浮夸、不做作值得思量。這不僅要求創作者在敘事上合理把控笑點與淚點、嚴肅與溫情,在問題的剖析和探討上也不能浮于表面。對于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可以巧妙帶過,但是在嚴肅的問題上需要警惕“搞笑”的遮蔽性,無厘頭的“搞笑”往往會帶領觀眾走向“不愿思考,一笑了之”的境地,最終導致問題流于表象。經典國劇《我愛我家》就是兼顧娛樂性與嚴肅性的代表,通過一家六口人的家庭瑣事,展現強烈的時代感,繪制出一幅波瀾壯闊的生活畫卷,其中,老傅這一角色時而仗著自己的輩分不講道理,干出一些驚人之舉惹得大家啼笑皆非,時而又成為“清醒擔當”,蹦出一兩句警世之言發人深省,讓人在發笑中頓有領悟。海外劇《無恥家庭》系列則以幽默、溫情的方式展現家庭日常生活,從不同性格家庭成員的瑣碎人生中挖掘出平凡生活中普通卻有趣、平淡又刺激的種種面貌,進而探討生命本身的意涵,觸動觀眾情感的同時又引人思考。
好的電視劇首先是觀眾愛看的。當“典型化+輕喜劇”的模式找到大眾審美與共鳴的“最大公約數”之后,我們的家庭教育劇能否往前再邁一步?當然,中國式家庭教育有其自身特色,并且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變化,聚焦此類主題的電視劇或許沒有太多他山之石可以直接套用,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但可以肯定的是,家庭教育劇不應只追求“典型化”帶來的呈現寬度,同樣需要注重對社會現象和家庭群體的挖掘深度。“輕喜劇”也不應淪為觀眾喜聞樂見的“萬金油”,帶來歡聲笑語之余是否可以注入一些嚴肅的冷思考。套路化無疑會扼殺家庭教育劇的創作想象力,“典型化+輕喜劇”的“組合拳”想要打好無疑對創作者提出更多的挑戰,不僅要對社會問題進行更加深入和與時俱進的探析,更要適配觀眾的欣賞個性與共性,注重藝術呈現的寬度與深度,讓家庭教育劇更好地“陪觀眾一起長大”。
(作者為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副教授)